写在前面:这是葛兆光教授的一本2011年新书,读下来只是觉得还不够痛快,对很多问题都展开论述了,但如此有趣的题目,要是能写成一部通史型的大部头著作该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以下是一些散记了。
本书大约告诉我们三个事情:其一,具体破解“中国”的概念的观念史的一些问题(不是连续的系统专著)。其二,介绍到很多本课题的研究史。其实,最近至少十余年间,“换一个角度看中国”成为国际史学的前沿话题之一,再有就是追溯到布罗代尔地中海巨著的区域史、社会史这两个思路仍然在史学研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比如衍生出来的所谓环境史学)。前沿感十分重要也是本书潜移默化传播的一种治学目标,这便是第三个事情。
“中国”一词的最早出现目前可查的是1963年出土的宝鸡西周何尊铭文“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薛(乂)民”,“中国”指天下之中的城市,应该是周东都洛邑。所以,中国的第一个概念是天下之中心的城市(国,指有城墙围合的地方)。之后,从《尚书》、《周礼》、《诗经》等文献开始,中国一词所指的内容成了中原地区,同时也开始成为中原文化、华夏文化的同义词,中国与四夷对称。这是中国的第二个概念,也是流传至今最重要的观念。再之后,随着秦统一帝国的出现和大汉王朝的强盛,汉人开始代指中原民族,而中国开始成为代指一个政府国家直到现在,这是第三个概念,也非常重要,但在传统时代其实没有前一个概念重要、只是到了20世纪才变得重要。子问题有很多,这里随便聊两个吧。
这里便有了关于民族国家等现代概念的冲突,比如,中国是否仅仅是在19世纪末叶遭到了外敌入侵的强烈冲击后才开始形成民族国家?这其实就是一个观念史问题而不是政治史问题。因为“民族国家”本身是欧洲近代史学出现的一个概念,其提出的目的是为了描述中世纪以后、尤其是文艺复兴以后欧洲各个以民族(文化性的,不是种族)概念和民族主义建立的政治国家、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中建立政体这一现象。民族国家在欧洲是一个具有历史偶然性的状态,也是演化的一种结果,不具有普适性和必然的先进性(在欧洲的政治进化中的确具有阶段性的先进性)。那么,用单一民族文化、确定国界来作标准的话,中国的确是很晚才成为民族国家的,但失去了历史环境的背景,这样的界定违反了历史学的基本原则。对于非洲和南亚的一些国家,的确是通过20世纪民族国家的建立改变了多民族长期分散的状态、尤其是被侵略和殖民状态,取得国家政治自由和经济发展上的一定改善。但如果仅从概念出发,我们会发现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成为民族国家的:宋代时期,由于周边非中原文明的辽、金、西夏、大理、土蕃等势力的强大,中原汉文化被挤压到大陆东南方向的一个相对狭小的地理空间,由于边界战争频繁暴发,所以有了非常明确的边境线;同时,逐步渗入的文化自卑感,少有的文化封闭的出现(宋真宗开始对历代向周边国家馈赠书籍的活动开始从鼓励或自由变为管制状态),甚至可以使得举国上下的国境概念也十分明确,因为周边的国家不再是臣服于中央王朝的、附属状态的政权,而明确的是“另一个国家”。而理学的出现,将儒学世俗化、常识化、甚至宗教化到每一个乡村、每一个国民的观念深处,直到今天我们生活中所谓的“封建残余”几乎都是朱夫子那个时代缔造的,这样强大的民族文化统一性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有力的。这样看来,宋代中国无疑是特征最明显的民族国家;如果加上宋代江南经济的特征或者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话,宋朝大概可以归结为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现代民族国家了吧?——这就是历史环境的归缪。
中国人对于外围世界的看法,最早就是“缚天之下莫非王土”,跳过中间的分分合合不说,蒙元帝国近乎没有边际的领土,和几乎半个地球的民族交流,使得中国同样从天下的观念中退了出来,人们对世界应该有了更开放的认识。西域人扎马鲁丁曾经向元世祖忽必烈进奉过一件叫做“苦来亦阿儿子”的西域仪器,据考证,这个发音是一个阿拉伯语单词的波斯语读法,而这个词便是“地球仪”,且据《元史》记载“其制木以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可见还是一个测量相当准确的地球仪。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人关于外国的历史知识其实已经远远不止于想象的西王母、也不是出访西域的少数传说了,海陆两条丝绸之路的交流在13世纪的一百年中连续的强烈冲击了全部中国社会。但之后呢?到了明代、清代,对于外国人的描述又经常退回到了想象的时代:明嘉靖时代的《三才图会》又大量出现了狗国、一臂国、穿胸国等数十种杜撰的国度和“真实”的见闻。利玛窦来华可能又一次改变了中国的观念,把人们从“天下”转到了“万国”。但在全社会而言,这一变化大约直到100年后的清乾隆时代才有所改观,但可能还只是存在于知识分子之中,对全社会观念的改变大概要到清光绪以后了。
所谓“换一个角度看中国”用作者之前提出的词叫做“从周边看中国”。很长时间以来,研究中国用的都是中国的材料;也就是说,无论中国的学者还是日本、美国的学者都是在甲骨文、敦煌文献、二十四史、四库全书的基础上去研究中国,而没有区域史或对话的概念,很少用过朝鲜的《燕行录》或者日本、越南的历史文档,更没有太关注历史时期其他国家或文化体对中国的看法以及观念的交流。略举一例。
在满清铁骑塔遍中原后,又一个“虏人”政权建立起来,这本没什么奇怪,但在康熙大帝的一朝之后,满汉融和的怀柔也好、文化消弭的疲惫也罢,总之,反清复明的少了、蓄辫安居的多了,汉民族整体就那么沉默了,这可能就是韦小宝式的悖论——小玄子和天地会到底谁是对的?为什么不能都是对的?最终,没有师徒兄弟情谊可说,皇上是对的。面对,这样的中国,朝鲜、日本其实有着极大的不满,认为大清中国不再是中华文明的代表,而遵从明朝服饰的朝鲜和日本则都自恃是伟大的中华文化的真正传人。在很多船员对话、商人聊天笔记中有着俯拾皆是的例子,更不用说像丰臣秀吉这样在明末就梦想建立一个以北京为中心的自己的大帝国的社会高层了。从此,思想文化的共同体彻底瓦解了,直到明治维新的刺激,日本自然而然的开始提出了“东亚”的概念,又要“脱亚入欧”,以至最后的“大东亚共荣圈”(有点像丰臣秀吉的构想,但观念上的关键是中心不再是北京而是东京!)。周边民族对于中国的观念也有着很多变化,就像我们在从镜子里看自己。
最后再说一点所谓前沿感。做学问和许多事情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吧。一个人们很喜欢引用的说法是陈寅恪先生借用“预流”名言,那是他在为陈垣《敦煌劫馀录》作序时所说的:“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近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意思是,做学术要不断抓住新材料和新问题,才算得上入流,否则就是不入流、不合格的。我们其实做其他事情、其他工作也要讲究“预流”,不断更新学习、跟上时代,否则就是被淘汰、不入流的。这里,需要说一下“预流”一词:其本意,是佛教用语:小乘佛教把果位分为四级,“预流果”是初级果位,比它高一级的是“一来果”,再高一级的是“不还果”,最高的是“阿罗汉果”。预,当介入、进入讲,同“干预”一词中“预”的意思,所以预流是入流、入门的意思,不是能够预见未来趋势意思。
杂说了许多,都是有感而发,不过,这本书本身虽然是专业史学,但还是很值得一读的。
2012年2月11日星期六
北京市潘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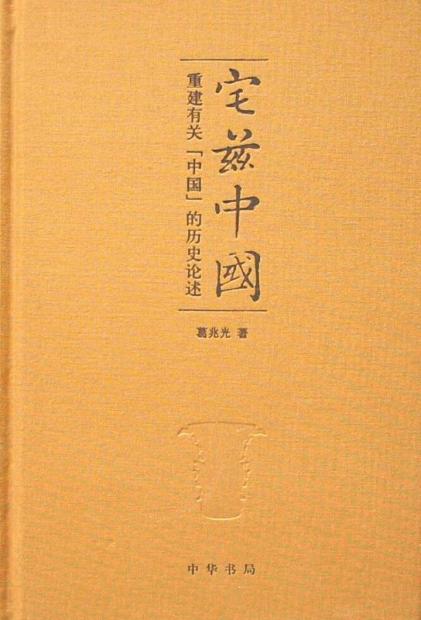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