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原版出版于1997年,是一个专门成立的委员会的专题报告。1990年代,美国教育改革,地理学学生增加较快,同时,地理学在信息化时代的发展方向如何,在这两大背景下,本报告的委员会组建于1993年,历经4年完成了这一报告。但报告的篇幅并不长,中译本的正文只有212页。
对于地理学,我们的印象中的概念大约就是地图、地名、区划分类。但对于山川河流、城市街道的认知,在信息化时代,已经全部可以通过计算机和互联网解决,无需大量的记忆为主要方式。其实,远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地理学的提出,无论是杜能、克里斯塔勒还是韦伯,都已经对地理学以知识积累为特征的古典学科范式进行了革命,使用数量、符号等抽象方式寻找地理学的学术本质。这一类知识向后传延为两个结果,一是所谓理论地理学,一是所谓新经济地理学。前者是地理学的方法论学科,引入了统计、数量模型等工具,但似乎与前辈们的工作差异不大;后者是198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开创的学派,旨在超越国际贸易理论,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做出修正,可以说是一次超越(克鲁格曼也因此获得2008年诺贝尔奖),但也使得地理学本来不够坚实的理论框架被经济学“侵略”甚至“瓦解”。现代地理学作为独立学科而存在的方法论是什么?难道只有以地理信息系统为代表的现代地图技术了吗?——当然,其实自然地理学的三大分支,生物地理学、气候学/气象学、地貌学由于研究范围的特定,各自都一套相对独立的概念系统和研究规律;学科危机更多出现在人文地理学范围的各个子学科。
本书的讨论包括对地理学的视角、地理学的教育(主要指在美国)、地理学的应用(决策、技术)等方面做出了分析评价和展望。
关于地理学的视角,如果说地理学就是通过空间关系观察世界,那么,似乎太失于笼统而等于没说(承认地理学的定义已经被当代学科所解构),因为这种方法没有具体的方法论,而研究对象有不特定,可以有各种“某某地理学”而没有了“地理学”。
首先,地理学的前沿视角可以是对“流”的认识,这是基于传统的“空间”的一种动态判别,是通过对空间位置特征的研究和位置间关系的研究而得出的动态分析。比如,植物分布、人口分布、物料流向、矿产分布与流动、甚至思想。有了“流”这一概念的统辖和相应的分析方法的确立,地理学才不屈从于被研究对象。
其次,地理学可以从“空间(space)”抽象化的拓展到“范围(range)”,这意味着对一些事件的结果,不仅要关注空间坐标的位置,还有关注其在概念系统中的位置。在不同情境下,泛洪平原的边界不同,作用也同样会有差别。水灾、气候变暖等地理概念都会有一定的动态变化,从而导致人地关系的不同和政策取向的差异。
第三,在人地关系,即人与环境的关系中采用“适应”的视角而不是遏制、改造。很多中国学者对此曾发出过推崇道家思想等中国传统文化的说法,似是而非,因为毕竟中西之间的思维体系差异很大,语词的意思不同。地理学所谓的适应在于对行为规律的研究,诸如面向移民问题,人口流动的特点如何,应该制定怎样的政策?城市规划的地理功能要素应该基于人口结构和特征,城市适应于人。这样的“适应”的概念是一种操作层面的,与“道法自然”式的中国文化旨在世界观和社会论的层面很不同。
卫星图片,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的发展,是地理学在资料上大发展的基础,但地理学不能反而因此下降为制图学,需要利用新技术提出概念,至少是操作性概念。好的地理学概念,比如,1930年代到1940年代,桑斯维特(Thornthwaite)在实验室设计了对大气需水量进行表征和估测的使用方法,即沿用至今的潜在总蒸发量模型、气候水分平衡算法。
人文地理方面,包括经济地理、社会地理、人口地理、城市规划等等。现代一些的概念,比如“地理可视化”,即将社会要素的“流”用带箭头的线表达在一张图上,或者其它更立体和复杂的方式。再如,区域人口运动分析,人口流动性和年龄组、就业率的关系,通勤强度与艾滋病感染率的相关性。这些题目的研究,背后的结论分析是来自社会学(含人口学)还是地理学呢?
1993年,相比于1980年代,美国大学中的地理学专业学生人数从10743人提高到15752人,增长46.6%,高于全国7%的增长率。而这一增长与同时期美国大学生女性和少数民族比例大幅提高有关(总体上,男生更多选择的自然科学类本科生都有所下降,而女性选择较多的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类都在增加)。
从该报告出版的1997年到现在又过去了15个年头,地理学的发展状态却仍大同小异,似乎没有方法论的革命,更没有像钱学森很早预计的那样出现地理科学为集合的复杂巨系统科学。学科的使命和核心方法论是一个学科兴起的关键,期待古老的地理学焕发新的生命。
2012年12月16日星期日
北京市潘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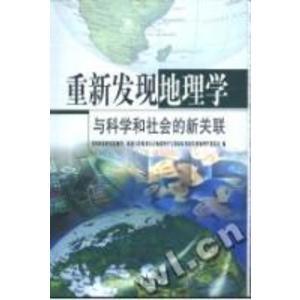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